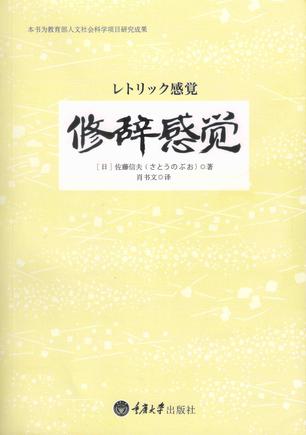
我一直在想,只用一句話,怎樣與修辭交心?
一流如張愛玲、魯迅,他們似乎毫不費力、信手拈來,美妙動人之辭句便從鋼筆尖兒,順著毛糙的紙面,勾連著,汩汩流出來,呼嘯著奔涌著,帶著一種叫做“文氣”的東西,擊中了紙面外捧著書的人,讀出了百年后一個一個不約而同的心事。
倘若世界毀滅,每個學(xué)科都只能留下一句話,物理是一切由原子組成,社會科學(xué)是雙盲實驗,語言學(xué)是人類靠隱喻認識世界,——那么修辭則是,修辭以立其感。
創(chuàng)造感覺,發(fā)現(xiàn)認識。
語言向來不是孤立的。我們以為,人類在一個溝溝壑壑的大腦里,思緒走了九萬八千里,搖搖又擺擺,孤身走上歧路、踏過獨木橋、拐入羊腸曲徑,尋尋覓覓,終匯入一條萬無一失的陽關(guān)大道——憑億兆后人在此馳騁生發(fā),向太陽無盡奔跑。語言落下,為思想蓋上鈐印,塵埃落定。不,不是這樣的。我們把一切想得太完美了。
思想沒有盡處,用語言以思考——語言乃思想本身。我思,故我在;我說,故我思。和朋友熱火朝天談天說地,想法會更多。思想從來沒說過自己是完美的。進化從來沒說過自己是完美的。或有豐碩的奇跡,那是一路上自然造化的饋賞。那是一條歸途,沒有目的。
「嘿,你在嗎?說話呀!」
「嗯,我在。」
「……」
「我一直在。」
只有語言,讓你明白思考了些什么。那是一個永遠前進的時態(tài)。前進,直到死亡,直到毀滅。
而修辭,是語言的思考方式。日出江花紅勝火,春來江水綠如藍,你用火與藍來思考江邊的花、春潮的江水。上善若水,你用水來思考善。半壕春水一城花,煙雨暗千家,半與一,煙雨籠罩下,千家暗淡。思君令人老,歲月忽已晚,我用歲月來思念,當我思念你的時候,歲月忽然紛紛過去了那么多,而我,因之思念,已垂垂老矣。
好修辭,能夠復(fù)現(xiàn)感覺。回憶會漸漸斑駁,一如容顏老去。感覺卻是最容易腐壞,容不得保鮮,下一刻永遠與上一刻不一樣,或更醇厚,或已酸變。人類在記憶長空中試圖抓住流水,即使徒勞,也想試一試。人類總是堅韌的,他們不放棄,便有了洋洋文辭,燦燦詩句。未曾老去斑駁的容顏鐫刻在了泛黃的詩句里,記憶里的一顰一笑,折下一枝梅花,斜斜倚著墻,釵頭的鳳凰將飛欲飛,還有千年以后的傷心人,與自己感懷同樣的哀傷。紅顏易老。紅顏未老。
「嘿,你在嗎?說話呀!」
「嗯,我在。」
「……」
「我一直在。」
「天涯明月共此時。」
「傷心同是斷腸人。」
那杯千年的濁酒溫了又溫。從麻紙,到宣紙,道林紙,電子紙……時光漫長無盡,而彈指一瞬。我與修辭交心,毋寧說是與人交心。與君同是傷心人,你我,從來不是一個人。
那時,要交出一篇《修辭感覺》或《修辭認識》的讀后感,我在圖書館的陽光里,只讀到了120多頁,苦著臉,絞盡腦汁。我向來是個跳脫不著調(diào)兒的人,卻想懸崖勒馬,好好寫出一篇讀后感,努力憋出了這篇讀后。回過頭,給自己打評價,只能說,小聰明,小文采。
現(xiàn)在,我終于讀完了《修辭感覺》,啃的時候覺得佐藤是個典型的中年日本文學(xué)教授,一絲不茍又不茍言笑,帶著精細的鑷子,眼眶里鏡片折出了日式柔光,帶著皺紋的手,用鑷子一點一點撥弄文字。很多修辭手法就生根在日常語言里,甚至于是對日常生活的模仿和再現(xiàn)。我們的耳朵就在修辭中培養(yǎng)語感。誰都不應(yīng)當拒絕修辭、懼怕修辭。修辭不應(yīng)當是標本,固定為“生動形象地寫出了 XXXX”的答題范式,隨著成長“哐當”一聲封存在灰暗里。它閃閃發(fā)光,眼里有慧黠,眼里有世間萬物。